探寻香格里拉——揭秘西方社会持续关注西藏的深层原因。
《寻找香格里拉——藏学、国学与语文学论集(一)》由沈卫荣撰写,将于202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聚焦于藏学、国学以及语文学等多个领域,展现了作者在这些学科中的深入思考与研究成果。作为一部学术论集,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中内容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也有对现代语境下文化传承的探讨,体现出作者对中华多元文化深刻的理解与关注。
>>内文选读:
寻找香格里拉——妖魔化与神话化西藏的背后
1933年,一位名为詹姆斯·希尔顿的人创作了一部名为《消失的地平线》的小说,至今仍广为流传,被后人誉为遁世主义小说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局势紧张之际,一个与世隔绝的乐土的故事。
1931年5月,外国人士正惊慌地从印度城市巴斯库撤离,一架由英国使馆派出的飞机原定飞往中亚的白沙瓦,却意外被劫持至一个名为香格里拉的地方。当时机上共有四人,包括英国公使罗伯特·康威(Robert Conway)、他的副手、一名女传教士以及一名正在被通缉的美国金融骗子。当这架飞机因被迫降在雪山之中后,他们意外发现这个被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竟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乐土。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当时国际局势的动荡,也让人对“香格里拉”这一神秘之地产生更多想象。它仿佛是一个现实与理想交织的避风港,令人不禁思考: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远离尘嚣的净土是否真的存在?抑或只是人们心中对安宁生活的向往?
雪山丛中,有一个名为“蓝月谷”的地方,中央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宫殿,最顶层居住着香格里拉的主宰“高喇嘛”(HighLama)。香格里拉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人才,其中有一位举止优雅、处事圆滑的汉族管家,还有一位美丽的满族小姐。香格里拉配备了中央供暖系统,设有俄亥俄州阿克伦产的浴缸,藏有庞大的图书馆,摆放着三角钢琴和羽管键琴,食物则从山下肥沃的谷地定期运送而来。
香格里拉的图书馆里面充满了西方文学的经典,收藏的艺术品里面有宋代的瓷器,演奏的音乐中竟有肖邦未曾来得及于世间公布的杰作,可以说世界文明的精华咸集于此。香格里拉的居民人人享受着现代、富足的生活,所有的西藏人却住在宫殿的脚下,他们都是伺候那些喇嘛及其他居民的仆人。除了西藏人以外,这里的人都长生不老。他们的“高喇嘛”已经活了250多岁。那位看上去很年轻的满族小姐实际上亦已经接近百岁了。
1919年,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美年轻一代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尤其是英国的许多精英知识分子和年轻人,他们怀着对人类社会美好幸福的憧憬,积极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战争摧毁了他们对世界的希望与梦想,使他们无法再回到传统的生活轨道上,于是开始在心中追寻属于自己的香格里拉。
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一场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其严重程度可能超过近年来我们经历的金融危机,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经济危机。可以想象,当战争摧毁了人们的理想时,又遭遇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该是何等的绝望与迷茫。随后,各国纷纷涌现出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以德国纳粹势力的崛起最为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逐渐逼近,民众对战争充满恐惧,饱受创伤的心灵渴望在香格里拉这样一个宁静美好的世外桃源中找到慰藉。
可以看出,香格里拉是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向往的理想乐土。
《消失的地平线》体现了当时的时代思想,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在看似纯净美好的乌托邦幻想背后,隐藏着诸多暴力与压迫。香格里拉被描绘成西方白人的理想国度,而非东方人的精神家园,更不是全人类的幸福之所。香格里拉居民的居住分布清楚地展现了这种表面上的和平神权体制下根深蒂固的种族等级制度:居住得越高,社会地位就越高,例如“高喇嘛”位于最顶层,是神权政治的最高统治者。外来的喇嘛们则居住在雄伟壮丽的雪山上的寺庙中,而大量种植粮食的土著居民则生活在山下的山谷中,这些人就是西藏人,他们除了吃饭、微笑和服侍他人之外,似乎再无其他作为。在香格里拉的社会结构中,他们处于底层,仅仅是仆役的角色。
西方一些人公开表示:“我们认为,由于西藏地区所处的高海拔环境等因素,藏族人在某些方面不如其他民族那样敏锐。他们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民族,我们也接收了不少藏族人,但对我们来说,怀疑他们中是否有人能够活到百岁。相比之下,汉族人情况稍好一些,但大多数人也仅能达到一般意义上的长寿。我们最优先考虑的无疑是欧洲的拉丁人和北欧人,美国人也同样受到欢迎。”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种族的划分十分明显,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
总而言之,香格里拉是一座西方文明的博物馆,是18世纪欧洲人对于东方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幻想。香格里拉是一个充满了帝国主义腐臭的地方,它是西方人创造的一个精神家园,而不是西藏人的精神家园。在《消失的地平线》中经常提到:东方人难以进行精神交流,西方人的精神苦闷和终极追求是东方人不能理解的。所以,这个保存了世界文化成果的香格里拉是西方文明的博物馆,东方文化只是装点。
1937年,著名导演Frank Capra将《消失的地平线》拍成电影,这部同名电影使得香格里拉的故事在西方深入人心。香格里拉本身的来历可能是作者灵机一动创造出来的,也可能是与藏传佛教里的香巴拉有些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作者知道藏传佛教里有香巴拉这个传统。总之,在地图里,香格里拉是一个找不到的地方,没有办法确定。从前美国的导弹发射基地就被称为香格里拉。美国总统休假的地方,现在叫戴维营,以前也叫香格里拉。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格里拉大酒店遍布东亚,但在西方是没有的。这是帝国主义的流风余绪,目的在于重温帝国主义的旧梦。
非常遗憾的是,几年前中国云南的中甸宣布自己就是香格里拉,同时也有不少人通过书籍等方式论证这个地方就是香格里拉。实际上,香格里拉原本只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如果将对香格里拉的这种认同作为一种发展民族经济的商业行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将云南中甸包装、浓缩为西藏文化的一个缩影,我认为是一种不合适的处理方式,这是在出卖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内部的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是为了迎合西方而按照西方的想象塑造一个东方的形象。这种倾向在近代和当代的电影、书画、文学作品中都曾出现过。
将香格里拉等同于西藏,是西方社会中一种典型的认知倾向,香格里拉逐渐成为后现代西方人心中的精神寄托。近年来,西藏及其藏族文化在西方广受欢迎,其根本原因在于:西藏被西方人视为香格里拉的象征,被整个西方世界构想为他们理想中的精神家园。这也正是西方持续关注西藏现象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多数西方人对真实的西藏缺乏了解,也并不真正关心现实中的西藏,他们所关注的是自己内心想象中的西藏,或者是虚拟化的西藏,而这种形象本质上是香格里拉概念的一种延伸与演变。
西方人对西藏的向往,是西方“东方主义”典型的表现之一。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西藏与现实中的西藏并无关联,它是一个被精神化、理想化的虚拟空间,承载着西方社会早已失落并渴望拥有的美好特质。这里被视为充满智慧与慈悲之地,没有暴力,没有欺骗与算计;藏族人则被描绘成一个绿色、和平的民族,人人平等,无阶级之分,无压迫与剥削。然而,这样的西藏在历史上从未真实存在,未来也极难实现。说到底,西藏是西方人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他者”,是他们用来反思自身的一面镜子,是他们在工业化之后寻找自我认同的参照点,是他们精神世界中的一个理想超市,寄托了他们的梦想与怀旧情绪。在这里,他们的精神可以自由驰骋,获得无限的满足与愉悦。与其说他们热爱西藏,不如说他们真正热爱的是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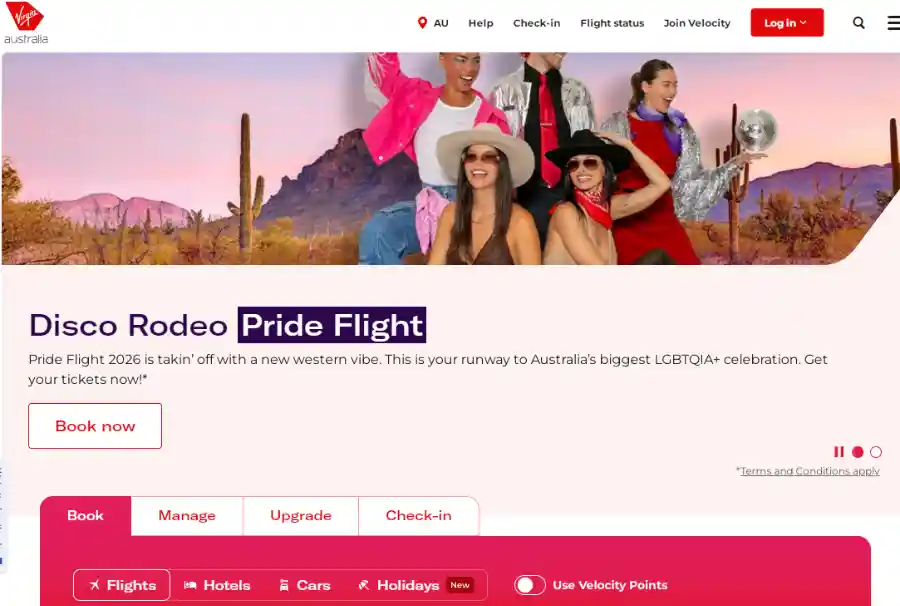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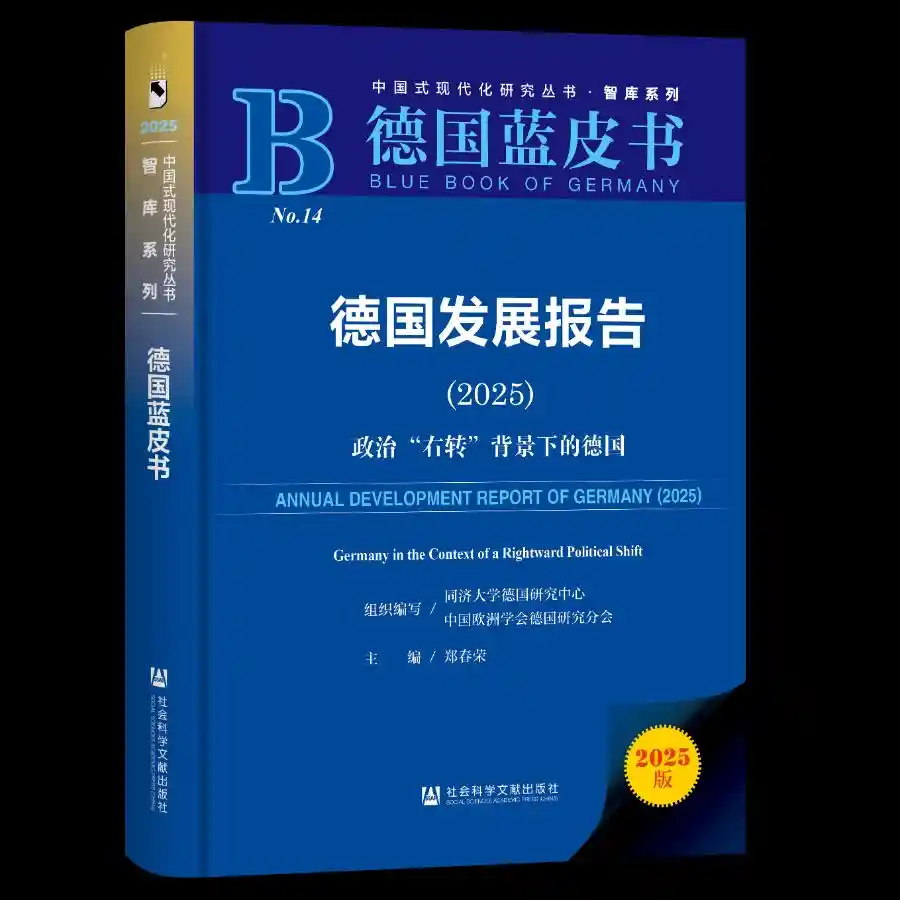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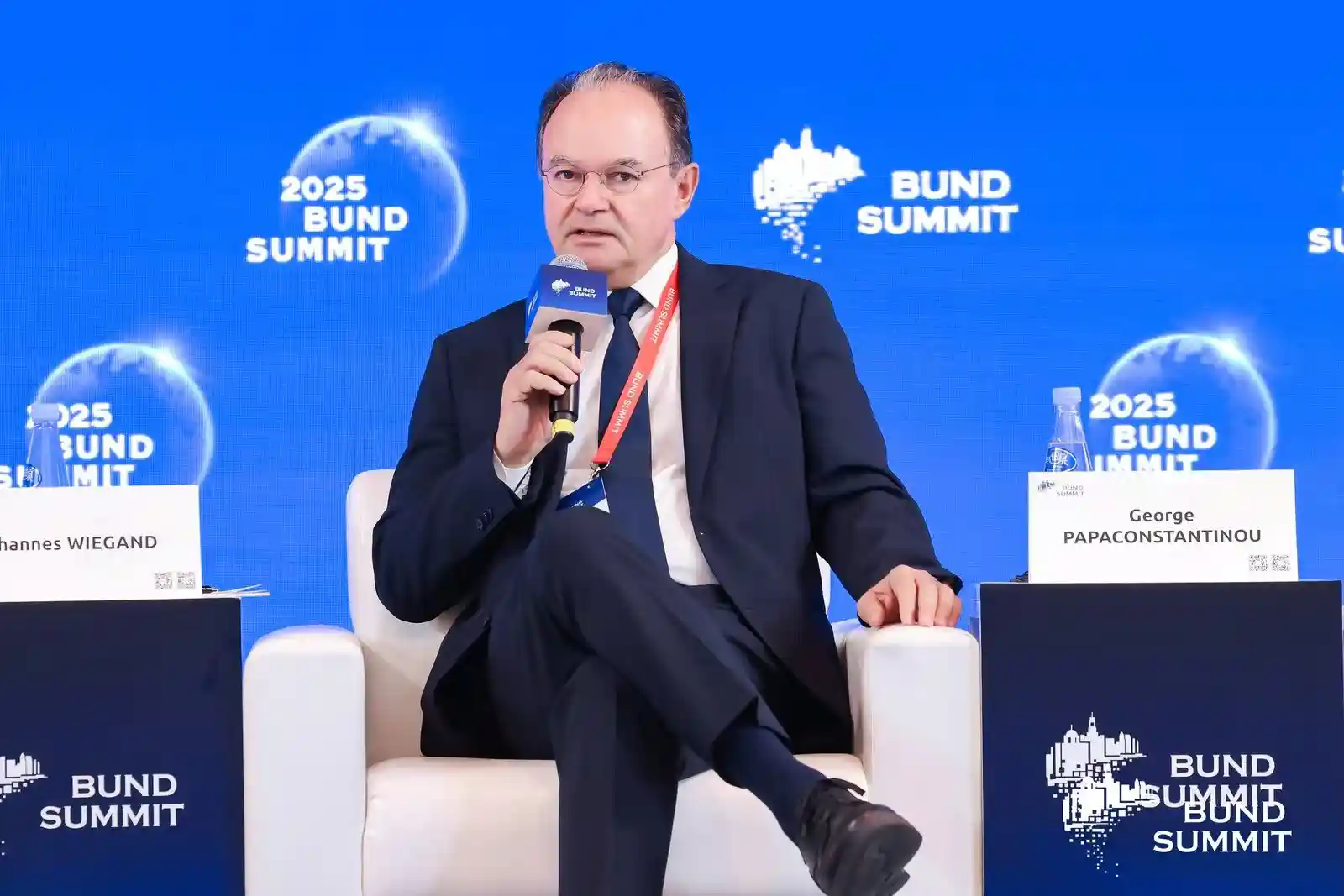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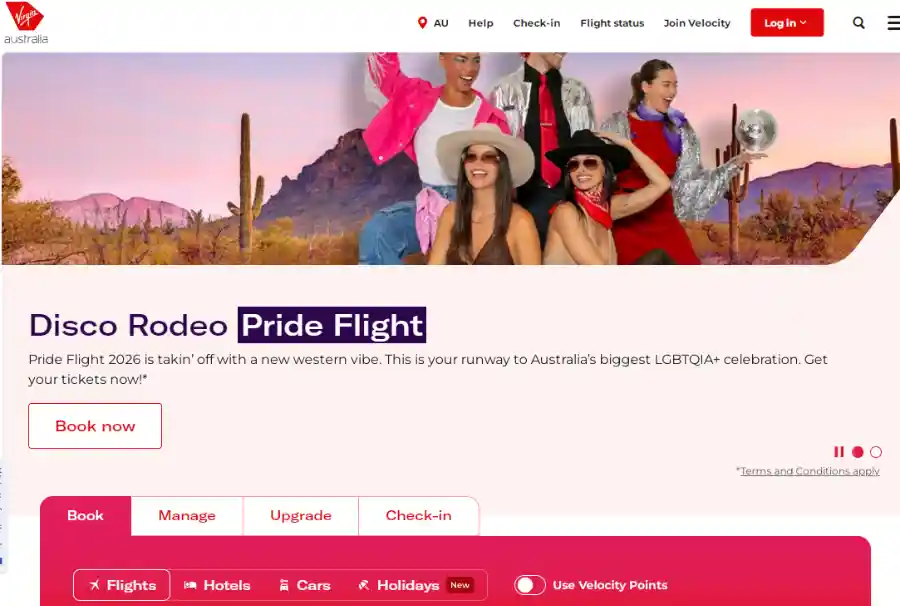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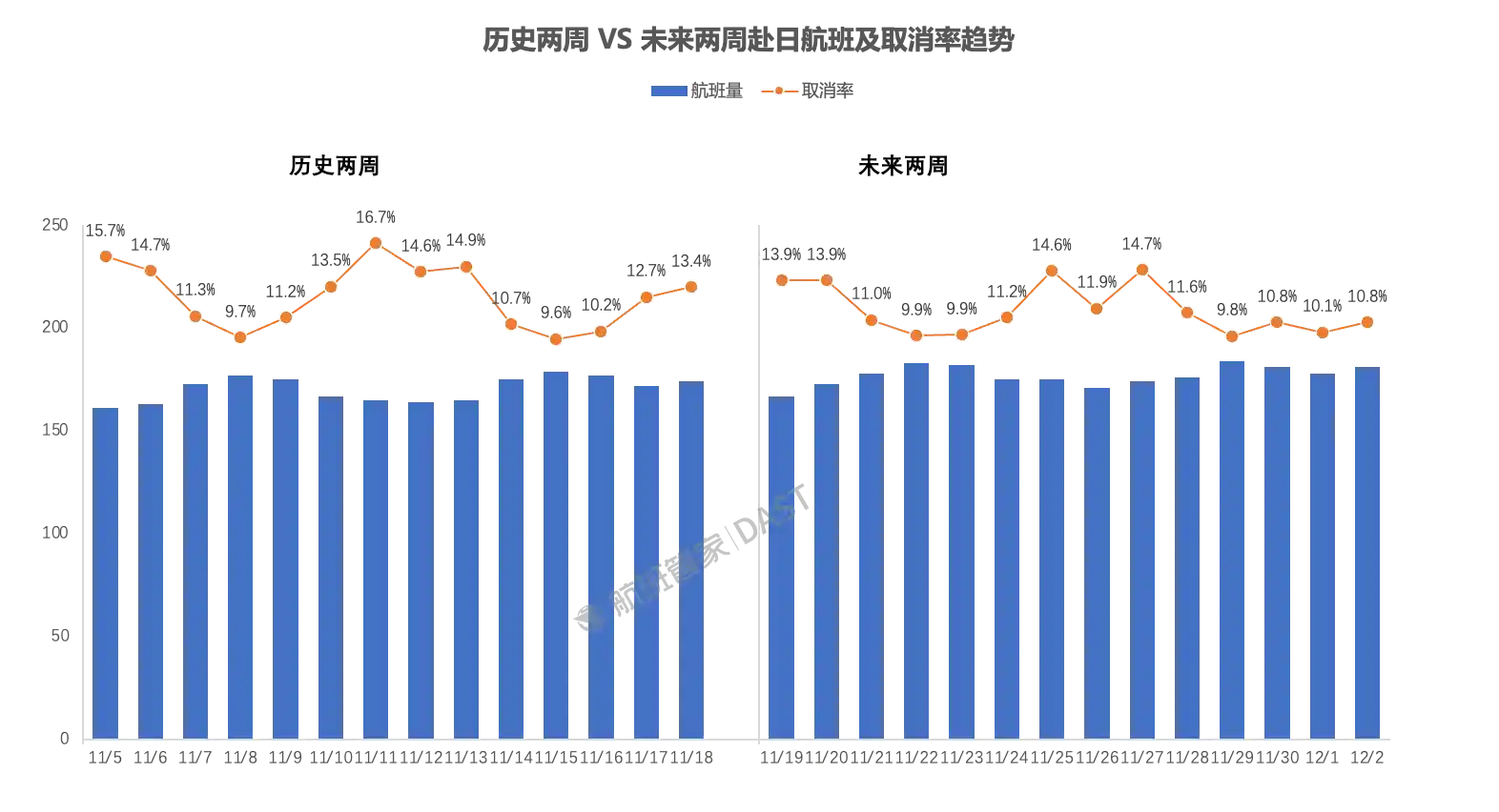






留言评论
(已有 0 条评论)暂无评论,成为第一个评论者吧!